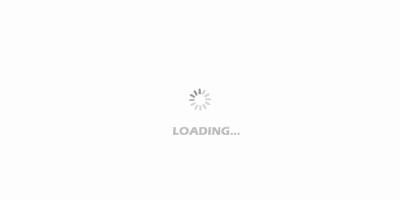前些時候在圖書館的時候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姑娘。
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漂亮——中長髮蓬亂地搭在一件最簡樸的綠色外套上, 皮膚有點黑, 兩頰上嘟嘟的有點肉。 但她是漂亮的——髮絲半掩的面頰上五官精緻, 尤其是有一雙美麗的桃花眼, 水汪汪。
我沒有蕾絲傾向, 所以一張同性的漂亮臉蛋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 真正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她所做的事情:面前攤著一本小書, 書頁右邊是一遝翻了一半的草稿紙。 姑娘雙眉緊蹙盯著紙上若有所思, 兩隻手在桌前上上下下緩慢地翻動。 判斷並不難做出——這個在圖書館閉館前二十分鐘還在或握起右手或張開左手並且看起來煩惱且困惑的姑娘是個理科女。
這個對自己的美貌一無所知的女孩, 她不在乎打扮, 不在乎裝束, 甚至某種程度上稱得上邋遢(我有提過她的頭髮看上去該洗了嗎?), 在一張自習桌前那麼認真和忘我。 她一直沒有抬眼, 也不在乎廣播中播放的閉館通知, 仿佛世界上剩下的只有面前的那本書和那遝稿紙。
就是這個女孩, 這個圖書館少女幫我解答了一個困惑很久的問題。 那天之前, 我看到了女記者瑪麗·科爾文的死訊, 又一時興起查了詩人蘭波的生平。 她和他是兩個讓我熱血沸騰而不能已的傳奇:瑪麗·科爾文是個戰地記者, 耶魯畢業, 報導過科索沃和車臣戰爭,
蘭波的名氣更大些, 這位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 神童, 銀幕上需萊昂納多來演的美少年, 十六歲出名二十歲封筆, 被同性戀情人大文豪維爾倫槍擊後從比利時走回法國, 後來販賣武器奴隸, 流浪在非洲並且最後在那裡患上毒疽死去。
出於某種原因, 我一直覺得這兩個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甚至不同性別的人, 有什麼地方無比相似, 正是那共性讓我心嚮往之, 讓我熱淚盈眶。 那天晚上我終於清楚它是什麼, 實則簡單直白——他們都在追尋中毫無保留, 忘我排他, 甚至飛蛾撲火。
一個耶魯畢業的金髮女郎,
他們之所以不同程度地感動我, 便是因為他們拋卻了“應該”。 “應該”二字是一個誘惑, 也像一把枷鎖。 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時代, 你我他“應該”做著這樣那樣的事情, 不過是將品格與能力一一剖開, 然後按需分配做這世界裡的一顆顆洋釘或螺母。
在我所眼見耳聞的情景裡, 格子間實驗室四大投行是一種“應該”, 爵士樂志願者騎行世界也是一種“應該”。
“她, 不就是一個電腦嗎?”師姐說。
“那, 喜歡旅行的人, ”我說, “不就是一輛自行車嗎?”
姑娘笑。
是有太多人, 覺得自己應該刷績點, 應該拼實習, 應該埋首程式與實驗室, 也有太多人, 覺得自己應該找靈魂, 應該去旅行, 應該投身山河與大自然。 事實上, “一種生活不見得比另一種更好, 而人應該遵循心靈的指引。 ”做《在路上》裡橫穿大陸自由不羈的薩爾有趣, 做《生活大爆炸》裡執著極客的謝耳朵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要是讓他們互換生活,
呐, 世間總有種種的路, 而我只有這一顆不能回頭的靈魂。 生活選擇和人生哲學是要多複雜, 說穿又是多簡單。
人生這麼短, 愛幹嘛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