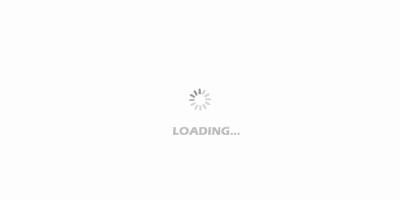2007年世界愛滋病大會, 何大一博士與同事一道正安靜的坐在觀眾聽著嘉賓的講解, 講臺上的宣講者在擺弄螢幕上的一幅卡通漫畫, 上面畫著一個被蒙上雙眼的棒球運動員正準備猛擊來球, 這個幽默細節讓何博士暗自發笑。 科學家們都很搞笑, 但他們也清醒得很, 他們知道畫面上那個盲目的棒球小子指的就是他們自己。 揮棒出去, 沒打中, 這場跟愛滋病搏鬥的戰爭已經打了很久, 但結果還是如此。
何大一可能讀懂了漫畫, 近1/4個世紀以來, 他和其他的愛滋病科學家們在同愛滋病的博弈中, 一次次被狡猾的愛滋病毒戲耍,
從2007年的愛滋病大會算來, 情況已經改觀了很多, 但要開發一種有效的愛滋病疫苗依然問題重重。 2009年情況出現了轉機, 科學家們宣佈他們開發出了一種新的疫苗, 這種疫苗表現出一定的抗病毒感染效果, 雖然這種效果只能算作一般;新疫苗能將愛滋病毒感染風險由原來的70%-90%降低到31%,
這些進展讓人備受鼓舞, 大家還依稀記得2007年的時候, 原本被寄以厚望能對付病毒的試驗失敗, 那種被打擊的痛苦記憶讓人永生難忘, 大家都以為沒指望了, 就像沒人能料到那場潰敗一樣。 科學界也暗暗鼓勁, 要從失敗的陰影中恢復過來, 哈佛醫學院的愛滋病專家布魯斯·沃爾克說:“要獲得一種有效的愛滋病疫苗, 能讓醫生們隨拿隨用, 我們還任重道遠。 ”
布魯斯的話的確有道理, 但何大一獨自發明了一種更像傳統療法的愛滋病疫苗,
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 在愛滋病領域還沒有人這樣幹過, 但何大一憑藉自己在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ADARC)二十年的研究經驗, 搭上自己的名譽也要毅然決然的賭上一把, 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也為此贊助了他700萬美元。
每當何大一談到這個新項目時, 嘴角都不由自主的露出一絲微笑, 實際上他肩上的壓力大到難以令他開顏。 90年代, 何大一革命性的率先使用抗逆轉錄病毒的雞尾酒療法, 降低了愛滋病人的死亡率, 同時也確立了自己以及ADARC在愛滋病研究領域的領導地位(何大一因此獲得了1996年時代年度人物獎)。 但最近幾年, ADARC卻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 論文被撤回, 重要科學家離開, 這些挑戰讓一些人對ADARC的前途感到擔憂:在這場對抗愛滋病的持久戰役中, ADARC和它的金牌帶頭人已經接近新的重大突破了,
抗艾第一人
不管何大一這次成功與否, 他在愛滋病領域長久以來建立起的權威形象不會受到動搖。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作為一名加州大學的醫師, 何大一開始為那些被推到急診室的病人做日誌, 這些病人都有一些奇怪的併發症狀, 如肺炎、癌症等, 更重要的是, 他們都發生了嚴重的免疫功能缺陷, 幾個月過後, 他發現了一個規律:大多數這樣的病人都是男同性戀。 隨著記錄的病例越來越多, 何大一對這種疾病也越來越感興趣。 兩年以後, 何大一和全世界都認識到這些人類首次接觸的病例就是後來讓人談之色變的惡魔:愛滋病。
當愛滋病還在讓其他科學家一頭霧水的時候, 何大一已經一步一步在這個領域開始了前瞻性的研究,他很快明白,期待未知才是對付愛滋病最好的法寶,很快在他身邊聚集起了一批該領域內的科學精英。當時有一批致力於愛滋病研究的專業研究中心成立,成立於1991年的ADARC也是其中之一,何大一出任中心主管,不久他領導的團隊前瞻性的提出了對愛滋病毒“早期打擊,從重打擊”的藥物治療方案,這就是雞尾酒療法的核心概念,這種療法救活了成千上萬的愛滋病患者。他的實驗室讓人們看到,在愛滋病毒感染新宿主的頭幾天或頭幾周內,迅速使用雞尾酒療法會起到極其明顯的效果。他們突破性的發現讓人們認識到,感染後坐等著幾年的潛伏期太消極了,愛滋病毒從第一天起就在活躍的攻擊免疫系統。之後不久,ADARC的科學家們又第一次向人們展示了愛滋病毒是如何通過一個次要的關鍵受體起作用的,病毒利用這個受體入侵細胞。
無效的疫苗
從新設計疫苗已被證明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愛滋病科學家們開始在藥物療法上尋找突破。儘管所有的科學家都瞭解愛滋病毒,但他們還是會漏掉一個關鍵細節,時至今日,他們還是不知道到底是哪種細胞或免疫系統能保護機體免受愛滋病毒感染;通過結合病毒的抗體來消滅病毒能取得成功嗎?通過特別改造能識別病毒大部分表面蛋白的T細胞來殺滅愛滋病毒的方法可行嗎?更或者,正如很多專家懷疑的那樣,將以上因素結合起來就能成功擊潰愛滋病魔?
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疫苗的開發也是步履蹣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加里·納貝爾說:“愛滋病毒是個活動靶子,因為它不僅通過突變不斷改變自己的遺傳結構,而且病毒表面的蛋白質會自己轉移,它們有靈活的空間構象。綜上所述,因此免疫系統無法識得病毒的廬山真面目。”
這些徒勞的努力使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隨時間慢慢流失,不光是在ADARC,到處都是這樣。何大一的研究團隊正在嘗試開發自己的疫苗,但同樣希望渺茫。據本世紀初離開ADARC的科學家說,該中心已經開始陷入科學低潮,缺少研究方向,完全不是當初因雞尾酒療法而贏得科學桂冠時的樣子;也有些人認為,年度人物評選惹來媒體的關注,何大一的管理風格也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中心的競爭氛圍開始加劇,一些人在關鍵項目上明爭暗鬥,研究轉入背地裡,生怕同事竊取了他們的成果。幾個高水準的研究人員(此處不方便透露姓名)開始心灰意冷,離開了ADARC。
離開的研究員之一,一位現任某所重點大學免疫實驗室的主任說:“在ADARC工作讓我獲益良多,那時對於我來說真是美好時光,這是我學術生涯中難得有的體驗。頭幾年中心的研究結構堪稱完美,學術氛圍也很濃,遺憾的是最終結局並不太美妙。”
何大一將實驗室中令人不適的氛圍歸咎為職員間的個性衝突,這種氛圍使中心的研究品質在下降。2002年,何大一認為他發現了由免疫細胞產生的X因數,這些免疫細胞幫助患者對抗惡化的愛滋病情,這一次他上了報紙頭條,但結果證明他的結論過於草率。何大一的實驗結果受到其他細胞干擾,他被迫發表了一份“撤回聲明”,宣佈撤回研究論文。“那真是一個令人尷尬的時刻,這是我們自找的,”何大一說,“我們的研究生涯大概到了一個低谷期。”
ADARC並不孤獨,其他愛滋病研究機構在疫苗研製上的努力也有了進展,但道路依然艱辛。默克研製的一種新疫苗,在2004年開始進行試驗,當時是吹得震天響,但三年後還是等來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這種疫苗不僅不能使人免受愛滋病毒感染,而且似乎還會增加感染愛滋病的風險。本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正在研發一種相似的疫苗,看到默克的結果,他們隨即推遲了針對該疫苗的研究。
“在這些結果被批露後一兩年裡,研究愛滋病疫苗的科學家們都活在淒涼無望的境地裡,”納貝爾說,“我們懷疑我們所做的一切,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情況不甚明朗
直到2007年早些時候,何大一才得以洞察到一些可能的答案。休斯頓Tanox生物科技公司開發的一種藥物令何大一非常感興趣,他對Tanox很熟悉,該公司的一位創始人就是他的朋友,同時他也是公司科學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因此如果公司的科學家們覺得有點眉目時,何大一亦認為值得一試。
他飛到休斯頓,聽了一場簡要彙報,內容即這種被稱為“ibalizumab”的新藥物,它是一種似乎能阻止愛滋病毒進入健康細胞的抗體。經過對大約200名愛滋病患者的前期試驗,這種藥物表現出一定的效果,但Tanox擔心病毒會產生藥物抗性。在愛滋病晚期病人身上,該藥物幾乎能清除血液中90%的病毒,但沒有人知道這種抑制效果會持續多久。Tanox公司的高層希望聽取何大一的意見,到底這種藥物值不值得進一步研究。
效果聽起來不錯,但何大一看到的並不僅僅是抗艾滋藥物大軍中又多了一員。愛滋病毒感染過程分為多步進行,而每一種抗逆轉錄藥物只能對其中的一步起到阻遏作用。CD4細胞是免疫系統的關鍵組分,Ibalizumab可以對病毒與健康CD4細胞的關鍵結合點起作用,它的這種介入效果可以防止病毒感染。如果Ibalizumab能有效打擊被感染病人體內的愛滋病毒,那麼它也許可以用來從源頭上預防愛滋病;換句話說,Ibalizumab可能成為一種全新的疫苗,傳統上我們需要搞清楚到底要利用免疫系統的哪一部分來打擊愛滋病毒,Ibalizumab則繞過了這個傳統。
何大一等不及報告結束就打電話回實驗室,讓研究員們馬上查閱關於Ibalizumab的相關文獻,黃耀星(音譯)接到了這個電話,他說:“何博士激動萬分”,何大一馬上從別的專案組調過來兩個研究員參與研究Ibalizumab,黃耀星是其中之一。苦等了近三年以後,這個好消息讓大家的研究熱情又重新高漲,ADARC在下東區的這兩層小樓一片歡欣鼓舞。
現在ADARC的科學家們全身心投入了一項工作:徹底弄清楚ibalizumab的作用機制以及如何去控制這種機制。CD4細胞有點像是免疫上的前哨網站,具有識別從普通的流感病毒到愛滋病毒等各種病原體片段的能力,並為它們打上標記以便其他細胞進行打擊。愛滋病毒一旦結合上CD4細胞,就可以通過一系列複雜步驟得以進入細胞內;如果Ibalizumab事先結合上CD4細胞,就能起到免疫陷阱的作用,通過這種作用來阻斷愛滋病毒進入細胞。具體說來,Ibalizumab能夠與CD4細胞受體結合,使得病毒無法完成必須的彎曲過程,這樣它就進入不了細胞內部,無法接管細胞的遺傳工廠來生產更多的病毒。
這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何大一被深深迷住了,但問題也依然存在,像這樣去約束CD4細胞也許並不是什麼好主意。使人體基本防禦體系的大部分停止運作意味著病人易於受到很多其他傳染病的威脅,愛滋病人一般都會盡力避免陷入這種免疫缺陷的境地。當何大一談起關於這個藥物的想法時,他的實驗室成員提出了上述的看法。
仙蒂·凡賽,另一位參與ibalizumab研究的ADARC研究員,同時也是一接待艾滋患者的臨床醫生,她說:“聽到這樣的想法,我的第一反應是,他是不是瘋了?把抗體放到CD4細胞上?這太可怕了,我們需要CD4細胞。”
但何大一相信,ibalizumab能作用得更為巧妙些。一般說來,CD4細胞就像是一個擁有幾個船塢的碼頭;愛滋病毒占了一個,ibalizumab占了另外一個,細胞還是有能力去對抗其他病原體。“如果說愛滋病毒的粘附位置是在CD4細胞的鼻子上,那ibalizumab則是在它的脖子後面,”何大一說,這意味著CD4細胞同ibalizumab的結合並沒有破壞它行使病原體標記者的能力,哈佛大學的沃爾克也說:“他們正嘗試去做的事情有堅實的科學基礎。”
目前,ADARC實驗室正在猴子身上進行試驗,確定ibalizumab是否能切斷愛滋病毒的感染,這些病毒不僅包括那些已經弱化的實驗室病毒株,而且還有天然毒株,目的就是要用感染能力最強的愛滋病毒去考驗ibalizumab抗體,如果它禁不起考驗的話,何大一馬上就停止這個項目,以免研究過於深入。
何大一當然不希望看到這種結果,但要像脊髓灰質炎疫苗、麻疹疫苗或天花疫苗那樣基於成功抗體不僅取得了一擊致勝式的快捷效果,而且徹底從治癒人群中趕走了疾苦,他也不抱這樣的幻想;相反,ibalizumab只是眾多用來打擊愛滋病毒的武器中的一種,同時最有效的一種。“當我第一次接觸到ibalizumab時,我就覺得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何大一回憶說,“這是我的直覺反應。”
當然,成就科學不能單單只靠直覺,何大一亦深知這一點,就像聰明的擊球手一樣,他希望憑藉直覺和專業技能的結合能引導他成功。對何大一來說,一擊必殺固然精彩,但他需要爭取的是一記全壘。
何大一已經一步一步在這個領域開始了前瞻性的研究,他很快明白,期待未知才是對付愛滋病最好的法寶,很快在他身邊聚集起了一批該領域內的科學精英。當時有一批致力於愛滋病研究的專業研究中心成立,成立於1991年的ADARC也是其中之一,何大一出任中心主管,不久他領導的團隊前瞻性的提出了對愛滋病毒“早期打擊,從重打擊”的藥物治療方案,這就是雞尾酒療法的核心概念,這種療法救活了成千上萬的愛滋病患者。他的實驗室讓人們看到,在愛滋病毒感染新宿主的頭幾天或頭幾周內,迅速使用雞尾酒療法會起到極其明顯的效果。他們突破性的發現讓人們認識到,感染後坐等著幾年的潛伏期太消極了,愛滋病毒從第一天起就在活躍的攻擊免疫系統。之後不久,ADARC的科學家們又第一次向人們展示了愛滋病毒是如何通過一個次要的關鍵受體起作用的,病毒利用這個受體入侵細胞。
無效的疫苗
從新設計疫苗已被證明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愛滋病科學家們開始在藥物療法上尋找突破。儘管所有的科學家都瞭解愛滋病毒,但他們還是會漏掉一個關鍵細節,時至今日,他們還是不知道到底是哪種細胞或免疫系統能保護機體免受愛滋病毒感染;通過結合病毒的抗體來消滅病毒能取得成功嗎?通過特別改造能識別病毒大部分表面蛋白的T細胞來殺滅愛滋病毒的方法可行嗎?更或者,正如很多專家懷疑的那樣,將以上因素結合起來就能成功擊潰愛滋病魔?
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疫苗的開發也是步履蹣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加里·納貝爾說:“愛滋病毒是個活動靶子,因為它不僅通過突變不斷改變自己的遺傳結構,而且病毒表面的蛋白質會自己轉移,它們有靈活的空間構象。綜上所述,因此免疫系統無法識得病毒的廬山真面目。”
這些徒勞的努力使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隨時間慢慢流失,不光是在ADARC,到處都是這樣。何大一的研究團隊正在嘗試開發自己的疫苗,但同樣希望渺茫。據本世紀初離開ADARC的科學家說,該中心已經開始陷入科學低潮,缺少研究方向,完全不是當初因雞尾酒療法而贏得科學桂冠時的樣子;也有些人認為,年度人物評選惹來媒體的關注,何大一的管理風格也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中心的競爭氛圍開始加劇,一些人在關鍵項目上明爭暗鬥,研究轉入背地裡,生怕同事竊取了他們的成果。幾個高水準的研究人員(此處不方便透露姓名)開始心灰意冷,離開了ADARC。
離開的研究員之一,一位現任某所重點大學免疫實驗室的主任說:“在ADARC工作讓我獲益良多,那時對於我來說真是美好時光,這是我學術生涯中難得有的體驗。頭幾年中心的研究結構堪稱完美,學術氛圍也很濃,遺憾的是最終結局並不太美妙。”
何大一將實驗室中令人不適的氛圍歸咎為職員間的個性衝突,這種氛圍使中心的研究品質在下降。2002年,何大一認為他發現了由免疫細胞產生的X因數,這些免疫細胞幫助患者對抗惡化的愛滋病情,這一次他上了報紙頭條,但結果證明他的結論過於草率。何大一的實驗結果受到其他細胞干擾,他被迫發表了一份“撤回聲明”,宣佈撤回研究論文。“那真是一個令人尷尬的時刻,這是我們自找的,”何大一說,“我們的研究生涯大概到了一個低谷期。”
ADARC並不孤獨,其他愛滋病研究機構在疫苗研製上的努力也有了進展,但道路依然艱辛。默克研製的一種新疫苗,在2004年開始進行試驗,當時是吹得震天響,但三年後還是等來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這種疫苗不僅不能使人免受愛滋病毒感染,而且似乎還會增加感染愛滋病的風險。本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正在研發一種相似的疫苗,看到默克的結果,他們隨即推遲了針對該疫苗的研究。
“在這些結果被批露後一兩年裡,研究愛滋病疫苗的科學家們都活在淒涼無望的境地裡,”納貝爾說,“我們懷疑我們所做的一切,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情況不甚明朗
直到2007年早些時候,何大一才得以洞察到一些可能的答案。休斯頓Tanox生物科技公司開發的一種藥物令何大一非常感興趣,他對Tanox很熟悉,該公司的一位創始人就是他的朋友,同時他也是公司科學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因此如果公司的科學家們覺得有點眉目時,何大一亦認為值得一試。
他飛到休斯頓,聽了一場簡要彙報,內容即這種被稱為“ibalizumab”的新藥物,它是一種似乎能阻止愛滋病毒進入健康細胞的抗體。經過對大約200名愛滋病患者的前期試驗,這種藥物表現出一定的效果,但Tanox擔心病毒會產生藥物抗性。在愛滋病晚期病人身上,該藥物幾乎能清除血液中90%的病毒,但沒有人知道這種抑制效果會持續多久。Tanox公司的高層希望聽取何大一的意見,到底這種藥物值不值得進一步研究。
效果聽起來不錯,但何大一看到的並不僅僅是抗艾滋藥物大軍中又多了一員。愛滋病毒感染過程分為多步進行,而每一種抗逆轉錄藥物只能對其中的一步起到阻遏作用。CD4細胞是免疫系統的關鍵組分,Ibalizumab可以對病毒與健康CD4細胞的關鍵結合點起作用,它的這種介入效果可以防止病毒感染。如果Ibalizumab能有效打擊被感染病人體內的愛滋病毒,那麼它也許可以用來從源頭上預防愛滋病;換句話說,Ibalizumab可能成為一種全新的疫苗,傳統上我們需要搞清楚到底要利用免疫系統的哪一部分來打擊愛滋病毒,Ibalizumab則繞過了這個傳統。
何大一等不及報告結束就打電話回實驗室,讓研究員們馬上查閱關於Ibalizumab的相關文獻,黃耀星(音譯)接到了這個電話,他說:“何博士激動萬分”,何大一馬上從別的專案組調過來兩個研究員參與研究Ibalizumab,黃耀星是其中之一。苦等了近三年以後,這個好消息讓大家的研究熱情又重新高漲,ADARC在下東區的這兩層小樓一片歡欣鼓舞。
現在ADARC的科學家們全身心投入了一項工作:徹底弄清楚ibalizumab的作用機制以及如何去控制這種機制。CD4細胞有點像是免疫上的前哨網站,具有識別從普通的流感病毒到愛滋病毒等各種病原體片段的能力,並為它們打上標記以便其他細胞進行打擊。愛滋病毒一旦結合上CD4細胞,就可以通過一系列複雜步驟得以進入細胞內;如果Ibalizumab事先結合上CD4細胞,就能起到免疫陷阱的作用,通過這種作用來阻斷愛滋病毒進入細胞。具體說來,Ibalizumab能夠與CD4細胞受體結合,使得病毒無法完成必須的彎曲過程,這樣它就進入不了細胞內部,無法接管細胞的遺傳工廠來生產更多的病毒。
這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何大一被深深迷住了,但問題也依然存在,像這樣去約束CD4細胞也許並不是什麼好主意。使人體基本防禦體系的大部分停止運作意味著病人易於受到很多其他傳染病的威脅,愛滋病人一般都會盡力避免陷入這種免疫缺陷的境地。當何大一談起關於這個藥物的想法時,他的實驗室成員提出了上述的看法。
仙蒂·凡賽,另一位參與ibalizumab研究的ADARC研究員,同時也是一接待艾滋患者的臨床醫生,她說:“聽到這樣的想法,我的第一反應是,他是不是瘋了?把抗體放到CD4細胞上?這太可怕了,我們需要CD4細胞。”
但何大一相信,ibalizumab能作用得更為巧妙些。一般說來,CD4細胞就像是一個擁有幾個船塢的碼頭;愛滋病毒占了一個,ibalizumab占了另外一個,細胞還是有能力去對抗其他病原體。“如果說愛滋病毒的粘附位置是在CD4細胞的鼻子上,那ibalizumab則是在它的脖子後面,”何大一說,這意味著CD4細胞同ibalizumab的結合並沒有破壞它行使病原體標記者的能力,哈佛大學的沃爾克也說:“他們正嘗試去做的事情有堅實的科學基礎。”
目前,ADARC實驗室正在猴子身上進行試驗,確定ibalizumab是否能切斷愛滋病毒的感染,這些病毒不僅包括那些已經弱化的實驗室病毒株,而且還有天然毒株,目的就是要用感染能力最強的愛滋病毒去考驗ibalizumab抗體,如果它禁不起考驗的話,何大一馬上就停止這個項目,以免研究過於深入。
何大一當然不希望看到這種結果,但要像脊髓灰質炎疫苗、麻疹疫苗或天花疫苗那樣基於成功抗體不僅取得了一擊致勝式的快捷效果,而且徹底從治癒人群中趕走了疾苦,他也不抱這樣的幻想;相反,ibalizumab只是眾多用來打擊愛滋病毒的武器中的一種,同時最有效的一種。“當我第一次接觸到ibalizumab時,我就覺得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何大一回憶說,“這是我的直覺反應。”
當然,成就科學不能單單只靠直覺,何大一亦深知這一點,就像聰明的擊球手一樣,他希望憑藉直覺和專業技能的結合能引導他成功。對何大一來說,一擊必殺固然精彩,但他需要爭取的是一記全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