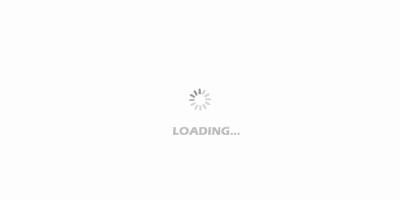關於中藥的由來, 一個公認的觀點是“源於生活實踐”, 一個基本的說法是“藥食同源”, 即古代先民為果腹之需, 往往饑不擇食, 其間難免會誤食一些有毒或有劇烈生理效應的動、植物, 以致引起嘔吐、腹瀉, 甚至昏迷、死亡。 經過無數次試驗, 逐漸形成了對某些動、植物可食或不可食的認識, 並又從中慢慢發現, 某種病痛發作時在吃了或誤食了某種動、植物後, 病痛得以減輕或解除, 進而有了藥物的認識和積累。 這就說明中藥與食物是同時被發現的, 藥、食之間起初並無明顯的或絕對的界線。 至於礦物藥的發現,
對於中藥起源及其功效認識的說法, 其實還存在著諸多疑問, 筆者茲提出有關思考與同道商榷。
現存最早的中藥學專著是約成書于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 該書顯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 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補充和完善過程, 是對其前的中藥學知識的整理與總結。
值得一提的是, 《本經》的話語體系與此前成書的《黃帝內經》已實現了基本契合, 彌補了《黃帝內經》方藥匱乏的不足。 對中藥功效確認的基本方法是以效定功, 即通過反復觀察應用後的反應, 來確定某種藥物的功能。 這一過程即使撇開受用者的年齡、性別、飲食、性情等複雜因素, 也還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使用單味藥物;治療同一病症;臨證反復應用。
縱觀中藥學史, 儘管有發展, 但對藥物的研究認識方法並沒有根本改進, 多是在《本經》基礎上的修訂、更正和補充, 且補充明顯多於更正。 也就是說, 後世本草大都沿用了《本經》的說法, 而補充的大量藥物——由《本經》的365種至《本草綱目》的1892種, 也同樣帶有過多的主觀因素, 對藥物功效的認識很多當屬於一家之言, 且有些認識經不起推敲與驗證。 如《本草綱目》中記述了很多未經系統觀察,
由於對單味中藥功效認識的不一致, 加之藥物配伍帶來的千變萬化, 這就給歷代醫家的臨床應用提供了見仁見智的機會。 中醫學豐富的臨床經驗中, 除了表現在對病證的病因病機的見解上外, 更多地還是見於選方用藥上, 即所謂用藥經驗。
用藥治病, 首要悉其性能。 清代醫家徐大椿形象地提出“用藥如用兵論”。 他指出:“兵之設也以除暴, 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 亦不得已而後用, 其道同也。 故病之為患也, 小則耗精, 大則傷命, 隱然一敵國也。 以草木之偏性, 攻臟腑之偏勝, 必能知彼知己, 多方以制之, 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孫武子十三篇,
關於這一點, 歷代醫家有頗多心得。 如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創制或記述的方劑, 用藥大都精當, 成為後世典範, 反映出他對所用藥物認識之精深。 李東垣對風類藥有獨到的認識, 在脾胃病中的應用頗顯匠心。 《景嶽全書》中有《本草正》2卷, 列常用藥300味, 但對人參、附子、熟地、大黃敘述尤詳, 並模仿儒家四維(禮、義、廉、恥)之式, 而將其稱為“藥中四維”。 當代醫家施今墨先生用對藥的心得, 焦樹德先生的《用藥心得十講》等, 對藥物的認知都可謂細緻入微, 表述生動貼切, 實用性很強, 值得研習效法。
此外, 一些醫家還有著鮮明的用藥特色, 表現為對某一藥物的偏愛,甚至為此而得新的稱呼,如“張熟地”(張景岳)、“嚴附子”(嚴觀)、“余石膏”(余師愚)、“陳柴胡”(陳平伯)、“烏梅先生”(劉鴻恩)、“石膏大王”(張錫純)、“祝附子”(祝味菊)、“徐麻黃”(徐小圃)、“嚴北沙”(嚴蒼山)、“陸黃芪”(陸仲安)、“石膏孔”(孔伯華)、“吳附子”(吳佩衡)等等。
然而,因缺乏明晰、嚴格的標準,系統細緻的臨床驗證,這類用藥經驗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簡單地照搬沿用很易致偏顯弊。
中藥普遍存在著“一藥多能”的現象,如黃芪有補氣升陽、益衛固表、利水消腫、托瘡生肌的功效,大黃有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止血、解毒、活血祛瘀的功效,仙鶴草有收斂止血、補虛、消積、止痢、殺蟲的功效等等。顯而易見,這應是由其性味、歸經或所含成分所決定的。客觀地說,以中醫學的認知條件和認知方法,能把藥物的功效認識到如此細緻,委實不易。
關於藥物功效的表述,古今有異者並不鮮見。如白芍一藥,《本經》謂之“味苦平,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其中的“利小便”在《傷寒論》的真武湯中即有所體現。而現行教材對此功效並未認定,言其能“養血調經,平肝止痛,斂陰止汗”。再如當歸,《本經》言其“主咳逆上氣”,而教材中也未採用。這種取捨不知所依何在?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無論是一藥一能或一藥多能,對這些藥之功效怎樣去驗證?因為臨床單藥治病幾無可能,而在複方中要驗證某一藥物的功效則難之又難。如此說來,尋找恰當的方法確認中藥的功效將是中藥研究中的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策。
對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一個時期以來研究中藥功效最常用的方法。原本是想通過對有效成分的分析,找出其功效的物質基礎,並認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一條可行之路。而多年的實踐卻證實,這種方法忽略了中藥成分的複雜性和整體性,除了有個別建立起了有效成分與功效的對應關係外,多數都未達到這一目的。一些中藥提取物,雖然在臨床治療中的針對性有所提高,但適應範圍卻大大縮小,嚴格說來已不再屬於中藥。
研究中藥的有效成分,無疑有利於對中藥功效的識別與認定,但這種將有效成分與功效對應的方法並不符合中醫學的原理,因而除非具有特異性功效而可辨病用藥外,如常山截瘧、茵陳退黃、鴉膽子殺阿米巴原蟲等,還是應強調辨證用藥,而對藥物的有效成分及藥理作用只能作為臨床參考。
目前,“中醫西化”現象很明顯,突出表現在對“病”的認識及對“藥”的運用上。不少醫者用藥的依據是病理而非病機、是藥理而非性能,在組方用藥時經常要考慮藥物的降壓、降糖、降脂、降酶、抗病毒、抗癌、強心等作用,割裂了理、法、方、藥的一體性,辨證論治的理念未得到體現,臨床自然難獲佳效。
毋庸置疑,現行教材及《藥典》中記述的中藥功效是經千百年應用認定的結果,是能經得起臨床檢驗的,但還遠未達到嚴謹、規範、清晰、無疑的程度。要實現這一目標,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系統整理古今文獻,力求去偽存真,從中發現確有價值的中藥功效,並通過規範的臨床研究加以驗證;建立符合中醫藥理論特色的中藥功效評價體系;將有效成分的研究與中藥功效的臨床研究有機結合;重視中藥功效術語的規範化研究。
表現為對某一藥物的偏愛,甚至為此而得新的稱呼,如“張熟地”(張景岳)、“嚴附子”(嚴觀)、“余石膏”(余師愚)、“陳柴胡”(陳平伯)、“烏梅先生”(劉鴻恩)、“石膏大王”(張錫純)、“祝附子”(祝味菊)、“徐麻黃”(徐小圃)、“嚴北沙”(嚴蒼山)、“陸黃芪”(陸仲安)、“石膏孔”(孔伯華)、“吳附子”(吳佩衡)等等。然而,因缺乏明晰、嚴格的標準,系統細緻的臨床驗證,這類用藥經驗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簡單地照搬沿用很易致偏顯弊。
中藥普遍存在著“一藥多能”的現象,如黃芪有補氣升陽、益衛固表、利水消腫、托瘡生肌的功效,大黃有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止血、解毒、活血祛瘀的功效,仙鶴草有收斂止血、補虛、消積、止痢、殺蟲的功效等等。顯而易見,這應是由其性味、歸經或所含成分所決定的。客觀地說,以中醫學的認知條件和認知方法,能把藥物的功效認識到如此細緻,委實不易。
關於藥物功效的表述,古今有異者並不鮮見。如白芍一藥,《本經》謂之“味苦平,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其中的“利小便”在《傷寒論》的真武湯中即有所體現。而現行教材對此功效並未認定,言其能“養血調經,平肝止痛,斂陰止汗”。再如當歸,《本經》言其“主咳逆上氣”,而教材中也未採用。這種取捨不知所依何在?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無論是一藥一能或一藥多能,對這些藥之功效怎樣去驗證?因為臨床單藥治病幾無可能,而在複方中要驗證某一藥物的功效則難之又難。如此說來,尋找恰當的方法確認中藥的功效將是中藥研究中的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策。
對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一個時期以來研究中藥功效最常用的方法。原本是想通過對有效成分的分析,找出其功效的物質基礎,並認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一條可行之路。而多年的實踐卻證實,這種方法忽略了中藥成分的複雜性和整體性,除了有個別建立起了有效成分與功效的對應關係外,多數都未達到這一目的。一些中藥提取物,雖然在臨床治療中的針對性有所提高,但適應範圍卻大大縮小,嚴格說來已不再屬於中藥。
研究中藥的有效成分,無疑有利於對中藥功效的識別與認定,但這種將有效成分與功效對應的方法並不符合中醫學的原理,因而除非具有特異性功效而可辨病用藥外,如常山截瘧、茵陳退黃、鴉膽子殺阿米巴原蟲等,還是應強調辨證用藥,而對藥物的有效成分及藥理作用只能作為臨床參考。
目前,“中醫西化”現象很明顯,突出表現在對“病”的認識及對“藥”的運用上。不少醫者用藥的依據是病理而非病機、是藥理而非性能,在組方用藥時經常要考慮藥物的降壓、降糖、降脂、降酶、抗病毒、抗癌、強心等作用,割裂了理、法、方、藥的一體性,辨證論治的理念未得到體現,臨床自然難獲佳效。
毋庸置疑,現行教材及《藥典》中記述的中藥功效是經千百年應用認定的結果,是能經得起臨床檢驗的,但還遠未達到嚴謹、規範、清晰、無疑的程度。要實現這一目標,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系統整理古今文獻,力求去偽存真,從中發現確有價值的中藥功效,並通過規範的臨床研究加以驗證;建立符合中醫藥理論特色的中藥功效評價體系;將有效成分的研究與中藥功效的臨床研究有機結合;重視中藥功效術語的規範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