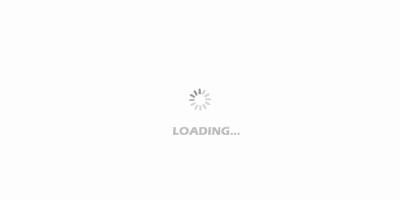養生之道網導讀:
明明是受害者, 卻慢慢認同了罪犯, 甚至主動幫助罪犯去實施犯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多數人知道“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說法, 源于這個詞曾被用在眾多備受關注的綁架和人質事件中——其中通常涉及到女性。
最常和這個詞聯繫到一起的是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 她是一份加州報紙的女繼承人, 于1974年被革命激進分子綁架。 但她似乎漸漸開始同情綁匪, 並參與了他們的一次搶劫, 最終被抓到且被判入獄。
但赫斯特的辯護律師伯雷(Bailey)宣稱19歲的她已被洗腦, 而且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個那時才被發明的詞,
這個詞最近被用在關於娜塔莎·坎普希(Natascha Kampusch)案件的媒體報導中。 坎普希在10歲的時候被沃爾夫岡·普裡克魯皮耶(Wolfgang Priklopil)綁架, 在一個地下室內被關押了8年。 但報導稱她在聽到綁匪去世的消息時哭了出來, 隨後又為躺在停屍間的他點上了一支蠟燭。
娜塔莎·坎普希被沃爾夫岡·普裡克魯皮耶綁架時只有十歲。
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廣為人知時, 讓它得名的事件卻依舊模糊不清。
瑞典之外, 很少有人知道貝吉塔·倫德布拉德(Birgitta Lundblad), 伊莉莎白·奧德葛籣(Elisabeth Oldgren), 克裡斯汀·恩馬克(Kristin Ehnmark)和斯文·沙夫斯多姆(Sven Safstrom)這幾個銀行員工的名字。
那是1973年8月23日, 這四人在信貸銀行(Kreditbanken)裡被32歲的楊·埃裡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扣為人質,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就從對此事的解釋中誕生。
警方狙擊手瞄準信貸銀行(Kreditbanken), 在那裡,
楊·埃裡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拘禁銀行員工作為人質長達六天。
據報導, 這個詞是由犯罪和精神病學家尼爾斯·貝傑茹特(Nils Bejerot)創造的。 在1970年代, 精神病學家弗蘭克·歐什柏格(Frank Ochberg)對這種現象產生了興趣, 且為聯邦調查局(FBI)和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定義了這種綜合症。
當時, 他正在幫助撰寫《關於應對恐怖主義和騷亂中的特別小組的報告》( US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errorism and Disorder)以發展應對人質情況的策略。
他的標準包含如下條件:
“首先, 人們會體驗到對他們突如其來的威脅, 他們註定會失去生命。
“然後, 他們會經歷一種幼化(infantilisation)——就像個孩子一樣, 未經允許就不能吃飯, 說話或者上廁所。 ”
微小的善意——像被施與食物之類, 暗示了一種“對給予生命的本能的感激”, 他解釋道。
“人質們會感受到對看押者有一種原始而充滿力量的好感。 他們會去否認是這些人造成了他們處境。 在他們看來, 正是這些人使他們能夠活下去。 ”
但弗蘭克也說,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案例是很罕見的。
那麼, 究竟在洛馬斯多雷廣場(Norrmalmstorg square, 即發生搶劫的銀行門前的廣場)上發生了什麼, 讓這些囚徒們不顧生命的威脅, 對綁匪們產生了好感?
在瑞典廣播電臺(Radio Sweden)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 當年人質之一的克裡斯汀·恩馬克解釋說:“身處那樣一種環境, 你所有的價值觀,
據報導, 也是人質恩馬克與劫匪奧爾森建立了最緊密 的關係。 甚至有失實的報導稱兩人在後來還訂婚了。
楊·埃裡克·奧爾森把銀行員工扣為人質, 關在銀行的地下室內
在一通從銀行地下室打給瑞典總理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的電話中, 恩馬克請求能和綁匪一塊兒離開銀行。 奧爾森其中的一個要求就是送一輛代步的車, 以便他和人質一起乘車逃走。 當局拒絕了這個要求。
一邊告訴總理帕爾梅自己對他“非常失望”, 恩馬克還說:“我認為你就是坐在那, 把我們的生命當棋子來玩弄。 我完全相信克拉克(Clark, 奧爾森的獄友)和奧爾森。 我一點都不絕望。 他們一點也沒傷害我們。 相反, 他們人很好。 但, 奧洛夫,
一年之後, 美國記者丹尼爾·朗(Daniel Lang)為《紐約客》雜誌採訪了涉及這場鬧劇的每一個人。 文章描繪了綁架者與被綁架者如何互動最全面的圖景。
他寫道, 人質說奧爾森對他們很好, 而且在當時, 他們似乎相信自己的命就是那兩個罪犯的。
有一次, 作為人質之一的幽閉恐懼症患者, 伊莉莎白·奧德葛籣被允許離開已經成為他們監獄的地下室, 但要有一根繩子系在她的脖子上才行。 她說那時覺得奧爾森真是“太好了”, 能允許她在銀行一樓走走。
另一個人質沙夫斯多姆說, 當奧爾森為了讓員警明白自己來真的, 說道準備對他開槍時, 他甚至心存感激。 不過奧爾森還補充說自己確保不會打死他, 並會讓他先喝點酒。
“當他對我們不錯時,我們可能把他當成了一個非常時刻的上帝,”沙夫斯多姆繼續說道。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常被用於解釋被關押者的矛盾的感受,但其實看押者的感受也發生了變化。
警方佩戴防毒面具,押送楊·埃裡克·奧爾森離開銀行
奧爾森談到他在剛被包圍時能很“輕易”地殺掉人質,但幾天後事情卻不大一樣了。
“我認為接受採訪的心理學家們忽略了一些事情:就像他們所說的,受害者可能會對施暴者產生認同,但事情不是單向的。”朗寫道。
“奧爾森語氣粗暴。‘這就是人質的錯,’他說,‘我說什麼他們都照做。如果他們不這樣,我也不會落到現在這個境地。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來攻擊我?他們搞的很難去動手殺人哎。他們弄的我們成天在一起,就像山羊一樣,繼續生活在那個屎地方。在那無事可做,只好去瞭解其他人。’”
謹以此圖獻給和我一樣看完阿婆小說完全鬧不清兇手和受害者名字的朋友們
罪犯能夠對被關押者表達積極的情感正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個關鍵因素,也是危機談判專家所鼓勵發生的。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的《執法快訊》(Law Enforcement Bulletin)中一篇文章的解釋,這種情感能夠增加人質獲救的機會。
儘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很早就被加入了警方的人質談判課程,但卻很難遇上,休·邁高恩說道。他曾在紐約市警察局工作了有35年。
邁高恩當過人質談判小組(Hostage Negotiation Team)的指揮官和首席談判專家。作為對一系列發生在1972年的人質事件的反應,小組於1973年4月成立。造成這些人質事件的銀行搶劫為電影《熱天午後》(Dog Day Afternoon)提供了靈感,並在紐約的阿提卡監獄(Attica prison)引發了一場以暴力收場的起義,以及慕尼克奧運會上的大屠殺【2】。
“要我說這種事存在挺為難的,”他說道,“有時在心理學領域中,人們會探尋某事的起因和影響,可它根本不存在。”
“斯德哥爾摩的情況很特別。它發生的時候,我們正好開始遇到更多的人質情況,而可能人們不想排除什麼我們也許會再次遇到的東西。”
他承認這個詞廣為人知,部分是由於其統一了人質談判中的心理學部分和警方部分。
對於鑒別這種綜合症,並沒有廣為認可的診斷標準,也就是與恐懼相關或與外傷相關的標準。而且它也沒有被《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和《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兩本主要的精神病學手冊收錄。
但有些精神疾病醫生也談到,其發揮作用的基本原則卻可以聯繫到不同情況之中。
“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家庭暴力,當某個人——比如一個女性,感到依賴她的伴侶,且和他呆在一起時,” 詹尼佛·瓦爾德說道,她是牛津大學諮詢門診的一名心理醫生。
“她可能會產生移情而不是憤怒。虐待兒童就是另一個典型——當父母從情感或肉體上虐待他們的孩子時,孩子卻傾向體貼他們,並且不去談論這事或者去為這事圓謊。”
四十年過去了,每當找到在公眾視野裡消失多年的被綁架者時,這個詞就會被提起。有人爭辯說,這暗含對受害者可能有的軟弱的批評。
在2010年《衛報》的一個採訪中,坎普希拒絕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標籤。她解釋說這病沒有顧忌到人們在特殊情形下會做出的理性選擇。
“我覺得你調整自己去認同綁匪是很自然的事,”她說道,“尤其是你花了很長時間和那個人待在一起的話。這事關移情和交流。身處一樁罪行裡,尋求常態可不是一種綜合症。這是一種生存策略。”
譯者注:
【1】克拉克·奧洛夫森(Clark Olofsson) 即下文提到的的克拉克,奧爾森向瑞典政府提出要他的前獄友克拉克進來,還有其他靠譜不靠譜的東西,尼瑪瑞典政府居然同意了,詳見維琪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rmalmstorg_robbery
【2】根據維琪百科,三個事件中,《熱天午後》靈感確實是來自1972年發生在布魯克林的一件銀行劫案,「阿提卡監獄暴動」則為《熱天午後》提供了一句經典臺詞"Attica! Attica!",阿爾帕西諾喊出這句是為了抗議警方亂用暴力,因為阿提卡監獄暴動就是以警方暴力鎮壓收場,死了不少人。至於阿提卡監獄暴動和「慕尼克大屠殺」,維琪上並沒有說和紐約的系列銀行劫案有關係,不知道是我沒理解這句還是作者碼字碼嗨了。
並會讓他先喝點酒。“當他對我們不錯時,我們可能把他當成了一個非常時刻的上帝,”沙夫斯多姆繼續說道。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常被用於解釋被關押者的矛盾的感受,但其實看押者的感受也發生了變化。
警方佩戴防毒面具,押送楊·埃裡克·奧爾森離開銀行
奧爾森談到他在剛被包圍時能很“輕易”地殺掉人質,但幾天後事情卻不大一樣了。
“我認為接受採訪的心理學家們忽略了一些事情:就像他們所說的,受害者可能會對施暴者產生認同,但事情不是單向的。”朗寫道。
“奧爾森語氣粗暴。‘這就是人質的錯,’他說,‘我說什麼他們都照做。如果他們不這樣,我也不會落到現在這個境地。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來攻擊我?他們搞的很難去動手殺人哎。他們弄的我們成天在一起,就像山羊一樣,繼續生活在那個屎地方。在那無事可做,只好去瞭解其他人。’”
謹以此圖獻給和我一樣看完阿婆小說完全鬧不清兇手和受害者名字的朋友們
罪犯能夠對被關押者表達積極的情感正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個關鍵因素,也是危機談判專家所鼓勵發生的。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的《執法快訊》(Law Enforcement Bulletin)中一篇文章的解釋,這種情感能夠增加人質獲救的機會。
儘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很早就被加入了警方的人質談判課程,但卻很難遇上,休·邁高恩說道。他曾在紐約市警察局工作了有35年。
邁高恩當過人質談判小組(Hostage Negotiation Team)的指揮官和首席談判專家。作為對一系列發生在1972年的人質事件的反應,小組於1973年4月成立。造成這些人質事件的銀行搶劫為電影《熱天午後》(Dog Day Afternoon)提供了靈感,並在紐約的阿提卡監獄(Attica prison)引發了一場以暴力收場的起義,以及慕尼克奧運會上的大屠殺【2】。
“要我說這種事存在挺為難的,”他說道,“有時在心理學領域中,人們會探尋某事的起因和影響,可它根本不存在。”
“斯德哥爾摩的情況很特別。它發生的時候,我們正好開始遇到更多的人質情況,而可能人們不想排除什麼我們也許會再次遇到的東西。”
他承認這個詞廣為人知,部分是由於其統一了人質談判中的心理學部分和警方部分。
對於鑒別這種綜合症,並沒有廣為認可的診斷標準,也就是與恐懼相關或與外傷相關的標準。而且它也沒有被《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和《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兩本主要的精神病學手冊收錄。
但有些精神疾病醫生也談到,其發揮作用的基本原則卻可以聯繫到不同情況之中。
“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家庭暴力,當某個人——比如一個女性,感到依賴她的伴侶,且和他呆在一起時,” 詹尼佛·瓦爾德說道,她是牛津大學諮詢門診的一名心理醫生。
“她可能會產生移情而不是憤怒。虐待兒童就是另一個典型——當父母從情感或肉體上虐待他們的孩子時,孩子卻傾向體貼他們,並且不去談論這事或者去為這事圓謊。”
四十年過去了,每當找到在公眾視野裡消失多年的被綁架者時,這個詞就會被提起。有人爭辯說,這暗含對受害者可能有的軟弱的批評。
在2010年《衛報》的一個採訪中,坎普希拒絕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標籤。她解釋說這病沒有顧忌到人們在特殊情形下會做出的理性選擇。
“我覺得你調整自己去認同綁匪是很自然的事,”她說道,“尤其是你花了很長時間和那個人待在一起的話。這事關移情和交流。身處一樁罪行裡,尋求常態可不是一種綜合症。這是一種生存策略。”
譯者注:
【1】克拉克·奧洛夫森(Clark Olofsson) 即下文提到的的克拉克,奧爾森向瑞典政府提出要他的前獄友克拉克進來,還有其他靠譜不靠譜的東西,尼瑪瑞典政府居然同意了,詳見維琪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rmalmstorg_robbery
【2】根據維琪百科,三個事件中,《熱天午後》靈感確實是來自1972年發生在布魯克林的一件銀行劫案,「阿提卡監獄暴動」則為《熱天午後》提供了一句經典臺詞"Attica! Attica!",阿爾帕西諾喊出這句是為了抗議警方亂用暴力,因為阿提卡監獄暴動就是以警方暴力鎮壓收場,死了不少人。至於阿提卡監獄暴動和「慕尼克大屠殺」,維琪上並沒有說和紐約的系列銀行劫案有關係,不知道是我沒理解這句還是作者碼字碼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