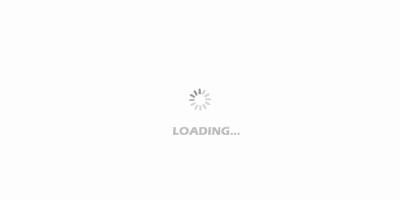一
他算不上好人。
從小就不好好讀書,
蹺課是常事。
15 歲更是連學也不上了,
跟一幫哥們混在一起,
抽煙、喝酒、早戀、打架。
唯一能讓寡母感到心安的是他還算孝順,
從 14 歲起小店每次要進貨都是他。
有眼疾的母親常常會歎氣抹眼淚,
混沌地看著狼吞虎嚥的他,
目光裡說不出是埋怨還是憐惜。
他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晃著,
有時候也去打打散工。
把掙來的錢給母親,
母親說留著給他娶媳婦。
他就笑,
說:“我才不急,
我的女朋友多著呢。
”
20歲那天,
一個女孩就找上門來,
挺著7個月大的肚子說是他的種。
他愣了,
本能地想跑,
女孩生了個女孩, 就是她。 胖胖的像只小粉豬。 她才3個月, 女孩就不見了。 躺在繈褓裡的她吧嗒著嘴巴, 他急得只打轉。 母親熬來米糊一點一點地喂她, 居然也沒瘦。 他便叫她:“朱小豬。 ”
二
那一天, 母親搭著梯子去閣樓拿貨一不小心滾落下來, 只來得及說了一句:“你是當爹的人了, 好生對你的孩子吧。 ”就溘然長逝。 那個時候他23歲, 而她剛兩歲。 她哭, 他也哭。
安葬了母親, 接過母親的小店外, 還有母親在時幾乎不離手的她。 他這才意識到, 養一個孩子比看一個店要麻煩太多。 開始, 他進貨時就把她扔在家裡。
那以後, 他去哪裡都帶著她。 進貨的時候, 她就坐在三輪車的貨物上, 咯咯地笑。 陽光照在他們的身上, 短短長長, 都是年華。
${FDPageBreak}
三
她要讀書了, 他領她去報名。 老師叫她寫名字, 她一筆一劃寫下:“朱小豬”, 老師們都笑了, 說這哪能當名字呢?她回頭看他, 他一臉窘相地搓著手。 一個老先生眯著眼說:“書中自有黃金屋,
一路上, 他不斷地喊她:“朱如玉”“朱如玉”, 不斷地說:“看, 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樣。 ”她卻嘟了嘴說:“我不喜歡別人給我取的名字, 你還是喊我‘朱小豬’吧。 ”他愣了。
雖然不喜歡那個學名, 但讀書還真是有天分。 尤其是數學, 加減乘除, 腦袋一轉答案就出來了。 很自然地, 她就開始幫他記帳。 他的兄弟多, 在小店買煙買酒經常先欠著錢, 而他也不好意思去要。 月底他一看, 說:“乖乖, 他們欠了我這麼多呢, 難怪我就賺不了錢啊。 ”
有一天, 幾個兄弟來小店要啤酒和一堆吃食, 吃完後拍拍屁股走人時, 她忽然拿著個小本子出來說:“你們還沒給錢呢!”他的兄弟們愣了,
她把錢一張張揀起來, 給他, 說:“欠你的, 就該還!”他詫異地看著她, 突然, 就笑了。 這一年, 她剛剛7歲。
四
小店的生意開始好轉, 鄰居就給他介紹了個女人。 女人比他大, 32歲了, 離婚, 沒有孩子。 不好看也不難看, 眼角略微吊著, 看著就有點凶。 他跟女人來往著, 有時候他還會去她那裡過夜。 而她做完作業自己睡去, 黑暗無邊地壓過來, 她在黑夜裡流淚。 心裡開始恐慌。 她知道那女人不喜歡她。
女人有時候也過來, 主要是到店裡去查帳。 有一次, 女人說帳目不對, 逼問她是否偷拿了錢。 她搖頭, 眼睛卻不看女人。 女人再問, 她還是搖頭, 眼神裡卻有些輕蔑。 女人火了, 抓起旁邊的一個電話簿劈頭蓋臉就打了過來。
她沒感到疼, 但是看到了很多血, 然後, 她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躺在醫院裡。 她看見他雙手捧著頭失神地望著她, 她喊:“爸。 ”他說:“別動, 你在輸血。 ”
她說:“我沒偷錢, 真的沒有。 ”他點點頭, 說:“我知道。 ”
女人走了, 據說是被他痛打了一頓。 他撫摸著她額頭的傷疤說:“我打了那麼多次架, 還從來沒打過女人。 ”
那以後, 他再沒有找過女朋友。
${FDPageBreak}
五
她的個子開始瘋長, 轉眼就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她從發育早的女同學那裡聽來了青春最初的啟蒙, 居然頗為鎮定地度過了第一次例假。看著他出出進進,心中忽然有點遺憾,到底還是有個媽好。只是,她究竟在哪兒呢?
二月春寒料峭。風吹在臉上有絲絲寒涼。她穿著粉色的棉夾克,在風中嫣然成一朵清麗的花。她很喜歡這件新衣服,試的時候就喜歡得緊,看一下價格竟要150元,就囁嚅著不敢說,戀戀不捨地脫下來。他眯著眼在一邊看著,說:“朱小豬長成大姑娘了,別說,還真好看。喜歡,爸就給你買。”他掏出錢來,一把碎票。到底是孩子,她拿了新衣歡快地在陽光下跳躍,動如脫兔。她回頭看他,他笑,頭上根根白髮。個子長得太快,總要買新衣,而他從來就沒有捨不得。
她知道小店的生意一直都很淡,能維持生計和她的學費就不錯了。她從來沒有問過,他給她買新衣的錢從哪兒來?
她讀的是重點中學,學校在市中心。那一天,中午放學,她跟一群同學一起湧出校門,突然有人喊:“看,蜘蛛俠!”她就跟著大家一齊看過去——川流不息的馬路對面新起了好幾座大廈,此時大廈外有人用根繩子拴住腰部正在上上下下地刷玻璃。這在當時的小城還是一件新鮮事。樓下已經有好多人在圍觀。她一邊和同學談笑一邊走過去,很不經意地一抬頭,愣了——是他!
二月春風似剪刀。臉上有了刀割一樣地疼。他穿得很單薄,寒涼的風吹著他的衣衫,吹痛了她的眼。她忍不住狂奔了起來,奔到無人的角落,拼命捶打著自己。
六
有一件事情,她沒有告訴他。半個月前,有個女人來找她,時髦的衣服裹著她略微發福的身子,女人伸出戴著大鑽戒的手摸她的頭說:“我是你媽媽。我現在過得好了,你跟我走吧。”她咬著嘴唇不說話,半晌才說:“不!”女人看她突然眼紅了,說:“你跟著他也過不上什麼好日子,跟我走吧,孩子。”她拗著頭,不讓眼淚落下來,說:“不。”女人欲言又止,沉默良久後,歎口氣說:“那好吧。我給你電話,你想好了就來找我。”
女人走的時候,迎春花開得正是蓬勃。女人回頭看她。她卻不看女人。那時她在想,爸現在在幹什麼呢?
現在看著他被吊在半空中甩來甩去地擦玻璃,這麼辛苦,她潸然淚下,覺得他的命真是苦,而自己母女欠他的真是太多。
她決心從現在開始,還他。
她拿出那張幾乎被揉碎的紙條,按照上面寫的,撥了那個異地的電話。她在電話裡說: “我可以跟你相認,但有一個要求,不要把這一 居然頗為鎮定地度過了第一次例假。看著他出出進進,心中忽然有點遺憾,到底還是有個媽好。只是,她究竟在哪兒呢?
二月春寒料峭。風吹在臉上有絲絲寒涼。她穿著粉色的棉夾克,在風中嫣然成一朵清麗的花。她很喜歡這件新衣服,試的時候就喜歡得緊,看一下價格竟要150元,就囁嚅著不敢說,戀戀不捨地脫下來。他眯著眼在一邊看著,說:“朱小豬長成大姑娘了,別說,還真好看。喜歡,爸就給你買。”他掏出錢來,一把碎票。到底是孩子,她拿了新衣歡快地在陽光下跳躍,動如脫兔。她回頭看他,他笑,頭上根根白髮。個子長得太快,總要買新衣,而他從來就沒有捨不得。
她知道小店的生意一直都很淡,能維持生計和她的學費就不錯了。她從來沒有問過,他給她買新衣的錢從哪兒來?
她讀的是重點中學,學校在市中心。那一天,中午放學,她跟一群同學一起湧出校門,突然有人喊:“看,蜘蛛俠!”她就跟著大家一齊看過去——川流不息的馬路對面新起了好幾座大廈,此時大廈外有人用根繩子拴住腰部正在上上下下地刷玻璃。這在當時的小城還是一件新鮮事。樓下已經有好多人在圍觀。她一邊和同學談笑一邊走過去,很不經意地一抬頭,愣了——是他!
二月春風似剪刀。臉上有了刀割一樣地疼。他穿得很單薄,寒涼的風吹著他的衣衫,吹痛了她的眼。她忍不住狂奔了起來,奔到無人的角落,拼命捶打著自己。
六
有一件事情,她沒有告訴他。半個月前,有個女人來找她,時髦的衣服裹著她略微發福的身子,女人伸出戴著大鑽戒的手摸她的頭說:“我是你媽媽。我現在過得好了,你跟我走吧。”她咬著嘴唇不說話,半晌才說:“不!”女人看她突然眼紅了,說:“你跟著他也過不上什麼好日子,跟我走吧,孩子。”她拗著頭,不讓眼淚落下來,說:“不。”女人欲言又止,沉默良久後,歎口氣說:“那好吧。我給你電話,你想好了就來找我。”
女人走的時候,迎春花開得正是蓬勃。女人回頭看她。她卻不看女人。那時她在想,爸現在在幹什麼呢?
現在看著他被吊在半空中甩來甩去地擦玻璃,這麼辛苦,她潸然淚下,覺得他的命真是苦,而自己母女欠他的真是太多。
她決心從現在開始,還他。
她拿出那張幾乎被揉碎的紙條,按照上面寫的,撥了那個異地的電話。她在電話裡說: “我可以跟你相認,但有一個要求,不要把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