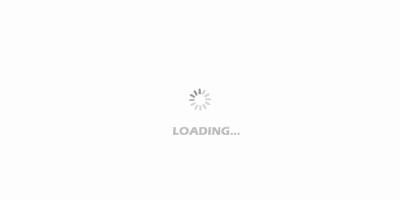讓-皮埃爾·溫特(Jean-Pierre Winter), 曾研習哲學和法律, 隨後轉向心理治療, 在巴黎佛洛德學院師從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83年, 他發起成立“佛洛德運動”組織, 現擔任該組織會長。 著有《肉體的漂泊》(Payot, 2001)和《文明的驚愕》(Pauvert, 2002)。
Jean-Pierre Winter:我可以明確地說, 這次危機的影響比以前都要來得快:有越來越多的人遇到了經濟困難。
■ 那您現在的來訪者肯定比以前少……
沒有!只不過他們的問題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聽到越來越多的人說, 他們感到了威脅, 覺得近期內可能失業、工資降低;或者擔心長遠的將來, 擔心孩子的未來不如自己。
■ 對此, 您如何解釋?
近幾年來, 在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領域, 大多數人都感到很多事情是徒有其表。 這次危機更讓大家意識到, 那些管理社會的人, 也就是所謂有權力的人和有知識的人, 或者擁有兩種權力的人(比如部長、企業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 他們只是裝出有知識、有權力的樣子。
■ 您想說危機引發出信任危機?
是的。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阿蘭·孟克(Alain Minc)之類經濟學家的種種宣言。
■ 信任危機對每個人會有什麼影響?
人們越來越不相信“有知識的人”真的有知識, 這讓人們覺得自己失去了武裝。 因為, 越是相信引領社會的人徒有其表, 人們的不安全感就越大。 這種信任危機還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人們開始詆毀教師階層。 年輕人在直覺上會覺得, 教師傳遞的知識就如同戀愛遊戲, 是為了引誘對方而作出的美麗欺騙。
■ 所以我們的問題變成座標缺失……
是的。 自由資本主義已經奪走了我們的一個基本座標——關於國家的座標。 近三四十年來, 佔據領導地位的說法都建立在197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密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論之上, 這個理論認為國家是萬惡之源。 他認為, 應該讓市場和競爭起主導作用, 人們可以對此保持信心。 現在, 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理論的經濟後果。 在心理層面上, 國家這個座標的消失, 會引起象徵功能的消失。
■ 就是說?
國家不是物質性的, 所以不能“指定”。 國家是你, 是我, 是我們所有的人, 以及許多其他元素。 所以,
■ 那後果會怎樣?會是超級個人主義?
是的。 因為國家起著連接個體的作用。 國家消失, 國民之間就失去了聯繫。 享樂主義就是個人主義: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角落自娛自樂。 個人享樂主義是有害的, 因為它會將死亡衝動、破壞衝動付諸行動。 當然, 個人不願意看到自身的死亡, 他會以攻擊的形式, 將這個願望轉向他人。
■ 帶有攻擊性的個人享樂主義和當前的危機有何聯繫?
它就是危機的中心!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是追求享樂, 追求積累的力量, 它驅使人們不斷追求更多的東西。 這種追求的結果是, 享樂與現實和物質相脫離, 變成自給自足的了。 在經濟領域, 這一點很明顯。 金融領域與生產的實際情況脫離, 不再反映實際的工作量。 然而, 與工作失去直接聯繫, 這意味著與欲望脫離關係。 我們在行動、生產和工作, 但不再有目標和欲望。 在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都能看到享樂和欲望之間出現了斷裂。 我們每個人都陷入吝嗇鬼邏輯:永遠要積聚更多的錢財, 並且不斷地消費。 這就是一種帶攻擊性的行為:消費, 首先就是吞噬。 可最後, 我們對什麼都沒了欲望。 因為欲望是什麼呢, 欲望不是可消耗的, 它的產生離不開缺失,欲望需要不斷更新。
■ 既然現有體系出現了這些限制,我們難道不該中止個人主義和暴力嗎?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平等,達到赫吉斯·杜勃雷(Régis Debray)所說的博愛。
看看現實吧。你在哪裡看到了博愛的群眾運動?我只看到一個個反抗的小群體。在企業裡,雇員們團結一致,但這種團結並不超出他們的工作領域。
■ 畢竟,我們感到大多數人支持反抗者,幫助他們,同情他們……
是的。幾乎所有人都支持他們,不過主要是在家裡的電視機前。如果我相信我在診所聽到的,那麼正好相反,危機起到了“減輕”的作用。
■ 減輕了什麼?
每個人身上都存在死亡衝動,但我們每個人都在盡力抑制這種衝動。突然,危機一來,我們找到了表達自身攻擊衝動的合法性。比如,有一位病人,提到因為危機喪失了財富的老闆們。他這麼跟我說:“他們活該!”還有一位,一說到美國的經濟衰退,就開始大呼小叫:“他們就該這樣!”即使我們有時有強烈的感覺,想要滿足攻擊衝動,但我們通常不會表現出來……除非在心理學家的診所裡,或者在危機時刻。
■ 那麼,我們離和平,離我愛人人、人人愛我還遠著呢……
是啊。赫吉斯·杜勃雷所謂的博愛,就是佛洛德所說的生本能(Eros),它一直在與死本能(Thanatos)做鬥爭。如果你讀過佛洛德的《文明及其不滿》,你就會知道生本能或者死本能都沒有取勝。因為生本能一直與死本能混雜在一起:生本能讓我們追求博愛以及與人的聯結,但它一直與死本能混淆在一起,以至於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永遠都不清楚,我們到底是被生本能支配還是被死本能支配。
我可以講一個在父親的服裝廠生活的小男孩的故事。睡午覺前,父親把西服外套套在了一個沒有胳膊的塑膠模特上。趁著父親睡午覺的時候,男孩把外套的袖子剪掉了。父親醒來後,火冒三丈。很多年後,男孩成人了,做心理分析時,他告訴我:他本來是想討好父親,他以為父親看到西服跟模特的身材很搭配會很高興。所以,在父親看來富有攻擊性的、應該得到懲罰的行為,實際上是男孩的愛的表達,當然這個表達有些糟糕。所以,追求博愛當然好,大家都應該希望生本能取勝。但這種美好的願望什麼都不能保證。作為精神分析師,我聽到更多的是致命的、有害的享樂,而不是善良的感情衝動。
■ 在中文和日文裡,“危機”這個詞也有“機遇”的意思。難道不會物極必反,從壞的情形下滋生出好的、有益的結果嗎?
經濟學家常常認為負面因素具有創造力。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曾說過: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但對於世界進程的這種解讀,是一種可怕的犬儒主義,也是一種暴力。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打著重新建構的旗號去進行解構。這就讓死本能佔據了發號施令的位置。沒有任何必要這樣去看待世界。說到這裡,我的腦子裡出現了痛苦的天才的形象:這種人認為如果不從自己的痛苦中汲取靈感,他就成不了天才。為什麼必須要否定自己或者其他人,才能成為天才呢?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佛洛德就是一個,他從來沒有吹噓過從自己的痛苦中獲得過什麼靈感,但終其一生他都是個天才。
■ 同意。但既然我們身處危機之中,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汲取教訓,試著改變心態,不是嗎?
當然,就像德國哲學家彼得·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說,解決之道就是“改變我們的生活”。這聽起來很好,但很難實施,除非滿足了一個先決條件:死亡衝動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絕不能忽視這一點,只不過不要讓死亡衝動佔據統治地位。只專注于充滿善意和慷慨的生命衝動,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就個體層面來說,我想到了一個例子。有一個病人,他在極其嚴格的天主教教育下長大,後來卻成了罪犯。為什麼?因為他的教育對他的要求,跟他強行壓抑的衝動希望他做的事情,相距太遠。
■ 那照您看來,什麼樣的體制會是一個好體制?
一個會考慮到死亡衝動的客觀存在,並對其進行限制,而不是禁止的體制。在最近幾年,出現了對於限制和禁止的混淆。所以,我們陷入了可怕的矛盾。比如,我們一面禁止在高速路上時速超過130公里,一面銷售時速超過280公里的汽車。這點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國家的象徵功能類似:國家的作用是限定享樂,是在博愛和個人主義之間找到平衡點。
■ 您覺得這次的金融危機跟精神分析的危機有關嗎?
自從精神分析問世的那一天,就存在著精神分析的危機。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為了避開精神分析最具破壞性的方面,極端自由化的體系催生出它所需要的治療門類。我指的 它的產生離不開缺失,欲望需要不斷更新。
■ 既然現有體系出現了這些限制,我們難道不該中止個人主義和暴力嗎?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平等,達到赫吉斯·杜勃雷(Régis Debray)所說的博愛。
看看現實吧。你在哪裡看到了博愛的群眾運動?我只看到一個個反抗的小群體。在企業裡,雇員們團結一致,但這種團結並不超出他們的工作領域。
■ 畢竟,我們感到大多數人支持反抗者,幫助他們,同情他們……
是的。幾乎所有人都支持他們,不過主要是在家裡的電視機前。如果我相信我在診所聽到的,那麼正好相反,危機起到了“減輕”的作用。
■ 減輕了什麼?
每個人身上都存在死亡衝動,但我們每個人都在盡力抑制這種衝動。突然,危機一來,我們找到了表達自身攻擊衝動的合法性。比如,有一位病人,提到因為危機喪失了財富的老闆們。他這麼跟我說:“他們活該!”還有一位,一說到美國的經濟衰退,就開始大呼小叫:“他們就該這樣!”即使我們有時有強烈的感覺,想要滿足攻擊衝動,但我們通常不會表現出來……除非在心理學家的診所裡,或者在危機時刻。
■ 那麼,我們離和平,離我愛人人、人人愛我還遠著呢……
是啊。赫吉斯·杜勃雷所謂的博愛,就是佛洛德所說的生本能(Eros),它一直在與死本能(Thanatos)做鬥爭。如果你讀過佛洛德的《文明及其不滿》,你就會知道生本能或者死本能都沒有取勝。因為生本能一直與死本能混雜在一起:生本能讓我們追求博愛以及與人的聯結,但它一直與死本能混淆在一起,以至於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永遠都不清楚,我們到底是被生本能支配還是被死本能支配。
我可以講一個在父親的服裝廠生活的小男孩的故事。睡午覺前,父親把西服外套套在了一個沒有胳膊的塑膠模特上。趁著父親睡午覺的時候,男孩把外套的袖子剪掉了。父親醒來後,火冒三丈。很多年後,男孩成人了,做心理分析時,他告訴我:他本來是想討好父親,他以為父親看到西服跟模特的身材很搭配會很高興。所以,在父親看來富有攻擊性的、應該得到懲罰的行為,實際上是男孩的愛的表達,當然這個表達有些糟糕。所以,追求博愛當然好,大家都應該希望生本能取勝。但這種美好的願望什麼都不能保證。作為精神分析師,我聽到更多的是致命的、有害的享樂,而不是善良的感情衝動。
■ 在中文和日文裡,“危機”這個詞也有“機遇”的意思。難道不會物極必反,從壞的情形下滋生出好的、有益的結果嗎?
經濟學家常常認為負面因素具有創造力。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曾說過: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但對於世界進程的這種解讀,是一種可怕的犬儒主義,也是一種暴力。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打著重新建構的旗號去進行解構。這就讓死本能佔據了發號施令的位置。沒有任何必要這樣去看待世界。說到這裡,我的腦子裡出現了痛苦的天才的形象:這種人認為如果不從自己的痛苦中汲取靈感,他就成不了天才。為什麼必須要否定自己或者其他人,才能成為天才呢?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佛洛德就是一個,他從來沒有吹噓過從自己的痛苦中獲得過什麼靈感,但終其一生他都是個天才。
■ 同意。但既然我們身處危機之中,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汲取教訓,試著改變心態,不是嗎?
當然,就像德國哲學家彼得·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說,解決之道就是“改變我們的生活”。這聽起來很好,但很難實施,除非滿足了一個先決條件:死亡衝動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絕不能忽視這一點,只不過不要讓死亡衝動佔據統治地位。只專注于充滿善意和慷慨的生命衝動,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就個體層面來說,我想到了一個例子。有一個病人,他在極其嚴格的天主教教育下長大,後來卻成了罪犯。為什麼?因為他的教育對他的要求,跟他強行壓抑的衝動希望他做的事情,相距太遠。
■ 那照您看來,什麼樣的體制會是一個好體制?
一個會考慮到死亡衝動的客觀存在,並對其進行限制,而不是禁止的體制。在最近幾年,出現了對於限制和禁止的混淆。所以,我們陷入了可怕的矛盾。比如,我們一面禁止在高速路上時速超過130公里,一面銷售時速超過280公里的汽車。這點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國家的象徵功能類似:國家的作用是限定享樂,是在博愛和個人主義之間找到平衡點。
■ 您覺得這次的金融危機跟精神分析的危機有關嗎?
自從精神分析問世的那一天,就存在著精神分析的危機。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為了避開精神分析最具破壞性的方面,極端自由化的體系催生出它所需要的治療門類。我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