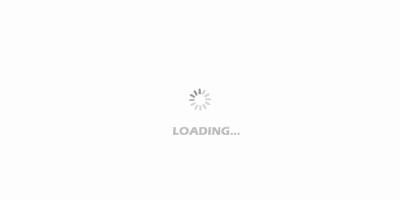十八、中醫師除了從自身廣袤豐富的臨床體會中, 還能從別的什麼地方獲得有關診治的經驗呢?對於我們來說, 重要的不僅僅“是什麼”, 而是去“做什麼”;“是什麼”只是一種狀態, 而只有去“做什麼”才能提供一種說服力。 《傷寒論》那些是不言自明的方證, 其中決定性的力量, 並不是來自“不言自明”的條文, 而是來自“我認為”。 “我認為”它不是自以為是的自我言說, 而是要經過打磨和歷練才會在嘗試中尋找到自己的聲音。
臨床實踐告訴我, 每當我們用仲景的“方證辨證”治好一個病案時, 我們覺得對《傷寒論》就增多一層的理解;與此同時,
汪丁丁說得好:“實踐之所以高於理論, 因為理論只是話語, 是等待著被人理解的文本, 是沒有實現的意志。 實踐則是理解的過程, 是實行中的意志。 ”所以醫學家也認為, 臨床實踐永遠是理論和學問的老祖宗。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醫師的個人經驗與學問的積累不都是正面的, 它同時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效果。 這些東西會使中醫師喪失了直接去感覺、判斷外在的鮮活的臨床病人的能力, 甚至喪失了這方面的興致, 變成一個以老賣老江郎才盡的“老中醫”。 所以中醫師永遠要保持對臨床的執著的熱情, 對病人高度的負責, 時時自覺地進行知識更新, 才會使自己的個人經驗與學問不會很快地蛻變老化。
十九、《傷寒論》自成理論體系, 從事經方醫學研究的人, 首先要下功夫學會經方系統內的知識, 學會運用經方思維去思考問題、診治病人。 一個經方學者, 如果沒有自覺地將自己融入《傷寒論》中, 他的所謂更換辨證思路也好, 他的所謂超越創新也罷, 不過是放縱自己的智力欲望而已。 當然, 卓然自立以後, 才能從容地去相容並收、擇善而從,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否則, 臨床上舉棋不定, 朝令夕改, 是難以治癒沉屙痼疾的。
二十、方證辨證的方法雖然是診治效果最好的一種療法。 但在我們沒有掌握它的精髓之前, 療效平平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種情況下, 選擇傳統的“辨證論治”於事無補,
矢數道明一針見血地指出:“諸家異趣, 技術不同, 故其立論制方亦各不同, 而摭拾雜亂, 則其方法不能統一, 而治療無規律矣。 ”即使醫生精通兩種不同思路的辨證療法, 也不一定是優勢互補。 在疑難病症面前, 將什麼“懸置”、“不提”、“放下”, 將什麼“堅持”、“攜帶”、“銘刻於心”, 是很難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致被從兩個方面來的相反力量扯得兩敗俱傷。 臨床事實常常告訴我們, 如果這樣的話, 只會使自己更加混亂和無能為力, 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更不得要領。 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跨越這種障礙, 在兩種旗鼓相當、互相抗衡的思路中遊刃有餘。 筆者的辦法是, 堅持“方證辨證”一種單一的辨證思路, 利用針灸等外治法,
現代經方醫師如果在紛繁複雜的臨床現象面前失去對症狀、體征、舌象、脈象的把握和病勢進退的方向感, 看不到各種變化中不變的東西——病人體質、病史和相應的方證狀態仍然客觀地存在, 則可能從根本上忘記了中醫經方醫生的使命。
二十一、強調經方醫學的獨立性, 是一個對於經方醫學自身合理性的訴求。 這項訴求的深遠意義並不在於宣佈經方醫學與外部世界脫節, 而是聲明任何經方醫學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給經方醫學提供任何現成的答案。
有沒有經過這個合理性論證是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需要經方醫學站在自身的立場上去思考人體生命醫學的諸多問題, 而不是站在其他醫學的立場去要求經方醫學。當然,很可能經過自我論證之後,經方醫學仍然也融入其他醫學的觀點,但這回是出於經方醫學的自願,出於經方醫學本身活力的考慮,而非一個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強迫。
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學派,不管是經方醫學還是醫經醫學,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它是一個有自身歷史的領域;有在長時間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有這個領域之內的人們所要面對的難題。在這個意義上,經方醫學是一道門檻,需要經過長時期恰當的訓練,才能得其門而入。大塚敬節從29歲(1929年)開始閱讀《傷寒論》,一生對《傷寒論》的研究從未間斷。他的宗旨是:研究漢方醫學始於《傷寒論》,並終於《傷寒論》。
二十二、理法辨證和方證辨證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它們追求的方向不一樣。方證辨證是追求“知其然”;理法辨證是追求“知其所以然”。
所謂“知其然”的方證辨證,是一種我們通過學習和模仿而獲得的有療效的辨證模式。這些模式發生的原因和機制人們至今可能還盲然無知,它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但我們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識到它們,並使自己的辨證方法與其相適應。就此而言,它又確實是我們理解病人病症的理性知識的一部分。這種使我們適應而採納“知其然”的方證辨證,同我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會有何種結果“為什麼”的知識——“知其所以然”的理法辨證極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把這種“知其然”的方證辨證,視為經方醫學。海耶克認為“知其然”之類知識的性質是處在人類的動物本能和理性之間——它超越並制約著我們的本能,但又不是來自理性。在人們一般想法中,“本能與理性之間”應當空無一物。“不是本能,就是理性,二者必居其一”,心理學上這種本能與理性二分法,使人們忽略了二者之間的那一片極其重要的領域,那是文明積澱傳承下來的非理性非本能的結果。這一見解,是海耶克的重要創見之一。
二十三、直言不諱地說,歷史以詭異的方式將中華民族的經方醫學移植在大和民族醫生的身上,移植在一個和我們文字、習俗、文化、制度等有很大差異的國度中。陰差陽錯,中醫經方的方證辨證在日本卻得到長足發展。日本漢方家把龐雜的中醫理論進行了“削盡陳繁留清瘦”的揚棄,竟然盡顯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東矣’一語,暗指這一令人難以啟齒的歷史事實。
目前對我們來說,學習和研究日本漢方是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200多年來日本漢方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錯誤和失敗,積累了運用《傷寒雜病論》方藥的超乎尋常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的確使人瞠目凝神,不勝感慨。因此學習日本漢方既是當務之急,更是長遠之思。當然,學習日本漢方應該有更冷靜的思考、更清醒的認識,表現出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機械地運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虛,賣弄和唬人,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基本的理論素養。有了這種素養,然後腳踏實地地觀察、研究我們自己的臨床物件,不斷提高臨床療效,做出更高水準的研究成果。總之,要以開放、理解、接納與包容的心態來看待世界,廣泛地接納日本漢方醫學的優秀成果。
二十四、張仲景宣導方證辨證的理念,具有無時空之分的普適性。但它在自己的故國一直處於隱匿的位置。當代經方醫學更是陷入到一種艱難的處境,它和現實發生了矛盾和脫節。現在,許多臨床中醫師對方證辨證都是非常陌生的,更使它的生存缺乏氛圍和土壤。這是一條多麼令人痛心的歷史下滑線啊。
中醫發展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醫臨床一旦切斷了和張仲景宣導的方證辨證的聯繫,就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幸好,在臨床中方證辨證的療效反復得到證明。可見它的深處尚積澱著歷史的自覺意識,這一令人可喜的意識,一定有一天能重新承載過去、接通未來,具有無限的發展空間。中醫經方醫學最好降低對中醫理性追求的熱情,全力遵循方證辨證規則下的診治,接受這些方證辨證規則下出現的東西,不論其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歷代經方家並不都是憑藉理性選擇了經方醫學,在更多的情況下,往往是由於親眼目睹經方神奇的療效,在情感上受到震驚而走上了經方之路。
二十五、《傷寒論》是古代醫學夜晚最動人的一場篝火晚會,其薪火穿越過兩千來年的歷史天空,至今仍舊光彩照人。也是《傷寒論》的火種點燃了日本漢方,使它升騰起燦爛的煙花。歷史進入近代,在東西兩種文明激烈碰撞中,中醫學滿目瘡痍,經方醫學的發展陷入低谷。黃煌、胡希恕撥開了重重的迷霧,使中醫界尋找到經方醫學存在的連續性和動力源,使人們對《傷寒論》有豁然開朗的領悟。
筆者相信,在未來的世紀裡,《傷寒論》會像一次輝煌的日出,給世界醫學增光添彩。張仲景的名字一定會鏤刻在未來人類共同體的紀念碑上。
而不是站在其他醫學的立場去要求經方醫學。當然,很可能經過自我論證之後,經方醫學仍然也融入其他醫學的觀點,但這回是出於經方醫學的自願,出於經方醫學本身活力的考慮,而非一個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強迫。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學派,不管是經方醫學還是醫經醫學,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它是一個有自身歷史的領域;有在長時間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有這個領域之內的人們所要面對的難題。在這個意義上,經方醫學是一道門檻,需要經過長時期恰當的訓練,才能得其門而入。大塚敬節從29歲(1929年)開始閱讀《傷寒論》,一生對《傷寒論》的研究從未間斷。他的宗旨是:研究漢方醫學始於《傷寒論》,並終於《傷寒論》。
二十二、理法辨證和方證辨證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它們追求的方向不一樣。方證辨證是追求“知其然”;理法辨證是追求“知其所以然”。
所謂“知其然”的方證辨證,是一種我們通過學習和模仿而獲得的有療效的辨證模式。這些模式發生的原因和機制人們至今可能還盲然無知,它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但我們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識到它們,並使自己的辨證方法與其相適應。就此而言,它又確實是我們理解病人病症的理性知識的一部分。這種使我們適應而採納“知其然”的方證辨證,同我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會有何種結果“為什麼”的知識——“知其所以然”的理法辨證極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把這種“知其然”的方證辨證,視為經方醫學。海耶克認為“知其然”之類知識的性質是處在人類的動物本能和理性之間——它超越並制約著我們的本能,但又不是來自理性。在人們一般想法中,“本能與理性之間”應當空無一物。“不是本能,就是理性,二者必居其一”,心理學上這種本能與理性二分法,使人們忽略了二者之間的那一片極其重要的領域,那是文明積澱傳承下來的非理性非本能的結果。這一見解,是海耶克的重要創見之一。
二十三、直言不諱地說,歷史以詭異的方式將中華民族的經方醫學移植在大和民族醫生的身上,移植在一個和我們文字、習俗、文化、制度等有很大差異的國度中。陰差陽錯,中醫經方的方證辨證在日本卻得到長足發展。日本漢方家把龐雜的中醫理論進行了“削盡陳繁留清瘦”的揚棄,竟然盡顯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東矣’一語,暗指這一令人難以啟齒的歷史事實。
目前對我們來說,學習和研究日本漢方是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200多年來日本漢方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錯誤和失敗,積累了運用《傷寒雜病論》方藥的超乎尋常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的確使人瞠目凝神,不勝感慨。因此學習日本漢方既是當務之急,更是長遠之思。當然,學習日本漢方應該有更冷靜的思考、更清醒的認識,表現出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機械地運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虛,賣弄和唬人,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基本的理論素養。有了這種素養,然後腳踏實地地觀察、研究我們自己的臨床物件,不斷提高臨床療效,做出更高水準的研究成果。總之,要以開放、理解、接納與包容的心態來看待世界,廣泛地接納日本漢方醫學的優秀成果。
二十四、張仲景宣導方證辨證的理念,具有無時空之分的普適性。但它在自己的故國一直處於隱匿的位置。當代經方醫學更是陷入到一種艱難的處境,它和現實發生了矛盾和脫節。現在,許多臨床中醫師對方證辨證都是非常陌生的,更使它的生存缺乏氛圍和土壤。這是一條多麼令人痛心的歷史下滑線啊。
中醫發展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醫臨床一旦切斷了和張仲景宣導的方證辨證的聯繫,就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幸好,在臨床中方證辨證的療效反復得到證明。可見它的深處尚積澱著歷史的自覺意識,這一令人可喜的意識,一定有一天能重新承載過去、接通未來,具有無限的發展空間。中醫經方醫學最好降低對中醫理性追求的熱情,全力遵循方證辨證規則下的診治,接受這些方證辨證規則下出現的東西,不論其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歷代經方家並不都是憑藉理性選擇了經方醫學,在更多的情況下,往往是由於親眼目睹經方神奇的療效,在情感上受到震驚而走上了經方之路。
二十五、《傷寒論》是古代醫學夜晚最動人的一場篝火晚會,其薪火穿越過兩千來年的歷史天空,至今仍舊光彩照人。也是《傷寒論》的火種點燃了日本漢方,使它升騰起燦爛的煙花。歷史進入近代,在東西兩種文明激烈碰撞中,中醫學滿目瘡痍,經方醫學的發展陷入低谷。黃煌、胡希恕撥開了重重的迷霧,使中醫界尋找到經方醫學存在的連續性和動力源,使人們對《傷寒論》有豁然開朗的領悟。
筆者相信,在未來的世紀裡,《傷寒論》會像一次輝煌的日出,給世界醫學增光添彩。張仲景的名字一定會鏤刻在未來人類共同體的紀念碑上。